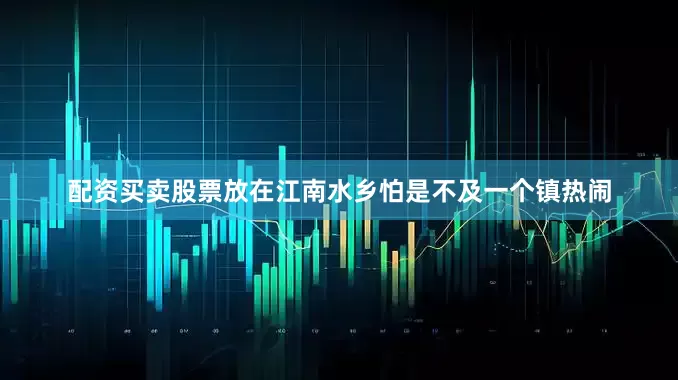
说起甘肃的行政区划调整,最近网上讨论得挺热闹的。不少人茶余饭后都在琢磨,要是能把几座城市重新“归堆儿”,是不是能整出点名堂来?尤其是酒泉和嘉峪关这对邻居,我去年自驾游走河西走廊,开车在两地之间跑,明明还没聊尽兴呢,导航就提醒我“您已进入嘉峪关市辖区”,真是近得叫人没脾气。
先说说酒泉和嘉峪关这哥俩。我住酒泉那晚,当地人跟我唠嗑,说嘉峪关是块宝地——那雄关漫道,那戈壁落日,哪个游客不慕名而来?但你说怪不怪,明明守着万里长城最西头的“名片”,嘉峪关自个儿要钱没钱、要人没人,发展步子就是迈不开。人口才三十来万,放在江南水乡怕是不及一个镇热闹。那么小的地盘,得养活整套市政府的班子,什么规划、建设、招商全得自己扛——想想都替他们喘不过气。

有人就大胆设想了:要是把嘉峪关整个划进酒泉,单设一个“嘉峪关区”, 会咋样?这个想法我听着确实有点意思。酒泉家底厚啊,全国闻名的卫星发射中心扎在那儿,通新疆、连内蒙的铁路公路四通八达。让嘉峪关轻装上阵,专心搞旅游开发和边贸,酒泉则在后面提供资金、人才这些硬支撑,这不比俩兄弟各自硬扛强得多?我在嘉峪关城楼晃悠时碰到个卖文创的大叔,他就嘀咕:“要是能借酒泉的东风把路修宽点、酒店建多点,咱这儿生意得翻几番!” 这种“酒嘉一体化”的构想,像是把宝剑配上了剑鞘—— 一个出鞘展锋芒,一个提供安稳支撑,劲儿往一处使,或许真能成甘肃的西大门户。
再往东瞧,金昌和武威的处境又另一番光景。 记得我在金昌街头看到个巨幅标语“聚金之川,昌盛之地”,倒是名副其实。这座城市简直是从矿坑里长出来的,家里真有矿!镍矿储量够全国用上百年的。我去矿山参观时,工程师挺自豪地说:“咱这镍产量啊,直接关系国家战略资源安全!” 但矿总有挖完的时候,再加上深处内陆、交通不便的硬伤, 金昌的焦虑写在脸上——转型的路该往哪走?

我看网上有声音提议让金昌当个“直筒子市”,也就是不设区的地级市。这想法透着股实用主义。想想看,金昌总共就一个金川区,人口四十多万, 规模真赶不上东部某些县。非得套个“区”的架子,办事得多绕几道弯?省去中间环节,市里直接对话街道,政策落地能快多少!关键是甩掉冗余行政成本,把资源集中到刀刃上——比如崆峒山那块的文化旅游开发,我上次在金昌博物馆看到那些远古岩画时就在想,这么好的文化家底,要是能打造成西北的“文化地标”, 配上特色矿冶工业游,不比单纯挖矿有奔头?毕竟地级市的“牌子”含金量更高,招商引资也容易开口子。
目光再转向省会兰州和邻居白银。 火车驶过白银时,望见那些林立的工厂烟囱和沉淀历史的老矿区,感觉特别复杂。这座城市曾经因矿而兴,也因矿而困。前些年盛传兰州想“吞”了白银,但这事儿一直悬着。有人担心:白银已经有点疲态,再失去决策自主权, 发展会不会雪上加霜?但也有人反驳:紧挨着省会就该借势!兰州的科研资源、消费市场若能对白银敞开,譬如让白银的精细化工搭上兰州高校的技术快车,让兰州人周末驱车一小时就能体验矿区公园的特色游,岂不是两全其美?这个度怎么把握,实在考验智慧。

当然,所有这些设想都得面对现实羁绊。行政区划调整就像个极其复杂的乐高工程——动一块积木,整个结构都得重新找平衡。 比如酒泉真接了嘉峪关这块宝,怎么调配有限的财政投入才显得公平?嘉峪关人会不会担心自己成了“二等市民”?金昌升级后那些铁饭碗会不会砸了?利益博弈像无形的线,牵一发而动全身。 前几年巢湖撤并的例子还在那摆着呢——效果是利是弊,到今天学界还在争论不休。
思来想去,我觉得甘肃的困境和出路其实像极了西部的戈壁滩——资源零零散散摆在那,怎么整合才能让绿洲连成片?这些行政区划调整的构想,甭管是酒嘉合体还是金昌升格,本质都是想破除人为的“边界墙”。有句老话讲得好:‘合则强,孤则弱’。 不过具体怎么合,步子该迈多大,恐怕没有标准答案。也许更关键的是思维方式:哪怕行政地图暂时不能改,各地管理者心里能不能主动拆掉无形的“篱笆墙”?比如嘉峪关主动对接酒泉的招商资源,金昌利用地级市的平台去兰州高校挖人才,白银直接把兰州的民生政策延伸落实… 让资金跟着项目跑而不是跟着级别走,人才顺着需求流动而不是圈在户口里—— 这些功夫下在看不见的地方,效果或许比生硬的撤并更长远。

说到底,西部要闯出一条新路,既需要敢想敢试的勇气,更需要脚踏实地的磨合。 行政区划调整与否,不过是手段而非目的。能让祁连山下的城市群抱得更紧些,让河西走廊的驼铃声里多几分现代经济的回响,才是千万甘肃人盼的真正春天。
炒股配资平台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


